一边红颜,一边妻子,林语堂的理想爱情:成功的婚姻,没有辜负的余地
林语堂在谈到婚姻时说:"既娶之,则爱之;既处之,则惜之映币。"他也切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个信念,将一桩老式的婚姻变成了一桩理想的爱情。
在《八十自述》一书中,林语堂有这样一句话:"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映币。"
他笔下的这个妹妹,就是陈锦端映币。二人的结识还要从他们的少年时代说起。
彼时,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他是学生中的翘楚,品学兼优映币。曾在大二学期典礼上四次上台领奖,出众的表现使他的名声渐渐传了开去。
而不远的圣玛丽女校也开始对这个才华横溢的才子有所耳闻映币。当时的陈锦端正就读于圣玛丽女校,她对这个出众的才子充满了好奇。而巧合的是,她的哥哥便是林语堂的同窗。
在陈锦端的哥哥陈希庆和陈希佐两人的介绍下,陈锦端和林语堂第一次见面了映币。
林语堂与陈锦端对视的第一眼,她的美丽与聪明便像一颗石子投射在他的波心,使他深深地沉沦了映币。"她生得确是奇美无比",林语堂这样回忆。陈锦端于林语堂来说,就是美的化身,又带着一股烂漫的孩子气,像灵动的精灵。
展开全文
而陈锦端也被这个才华横溢又出落得如此英俊的男孩吸引住了映币。他们常常齐坐在湖泊边的草地上,一边望着水天相接之处,一边聊天,谈文学、谈诗歌、谈艺术、谈哲思与信仰……
他们的灵魂映着水色和天光感受到了彼此那股强大共鸣的力量,讶异于彼此之间惊人的契合映币。
于是,他们在这个最美好的年纪拥抱了彼此映币。
陈锦端出身名门,父亲是归侨名医和当地富商,家财底蕴深厚映币。她的家长感受到了深深的威胁——一个牧师的儿子,奈他再有才,也不可能同自己的女儿相配!陈父找来林语堂,不客气地说:"我已为陈锦端定了亲了。"林语堂深受打击,在暗无人迹之处哭得泣不成声。
就这样,林语堂和陈锦端如图隔河相望又无桥可渡的恋人,绝望而无奈映币。但陈锦端的父亲还是很看好这个聪明的男孩,他将隔壁廖家的女儿引荐给了林语堂。
林语堂面对无法得到的爱情,只得发出一声悠长的慨叹:"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映币。"
林家父母对廖家的女儿廖翠凤十分满意,满心欢喜地催促林语堂前去提亲映币。二十出头的林语堂,不愿与父母作违抗,就此去了廖家。
廖翠凤或许并不如陈锦端那样怀着对艺术人生的一腔痴情,却也是个十分聪明果敢的女子映币。廖翠凤对林语堂的才华早有耳闻,她听说林语堂来登门提亲,便躲在屏风后,悄悄地看着。她看见了一个无拘无束的青年,一表人才,谈笑风生,衣着随便,而胃口极好,她禁不住地欢喜。
但是,这时候轮到廖家起了担忧映币。廖母问廖翠凤:"林家太穷了,怎么办?"廖翠凤却干脆而坚定地回答:"穷有什么关系?"林语堂听闻,更决心自己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个女子。
1919年,二十四岁的林语堂娶了陈家隔壁的廖翠凤映币。婚礼过后,林语堂对廖翠凤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时才用,我们烧掉吧,今后用不着它。"得到廖翠凤的同意后,林语堂便把婚书投入了火中。
这是林语堂对一个女人和一段婚姻的坚守和决心映币。
从嫁给林语堂的那刻起,廖翠凤就决定为林语堂建立一个家——"她像个海葵,牢牢地吸在一块石头上,吸住不放,这石头就是她的生命映币。石头如果迁移到哪里,海葵也跟到哪里。"
林语堂带着妻子廖翠凤一同前往哈佛映币。在那里,林语堂一早就去学校,不上课就扎进图书馆。而廖翠凤买菜、烧饭、洗衣,精打细算地用好每一分钱币。
林语堂也不曾冷落了妻子映币。廖翠凤盲肠炎发作的时候,他陪在她身边,安慰她这只是个小手术。出院时,暴雪纷飞,街上不好行车,语堂便借来一架雪橇,拉她回家。
后来由于清华经费变故,林语堂的留学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映币。廖翠凤为维持二人生活,将自己的首饰一件件变卖了。由于国外的中国首饰行情并不好,廖翠凤有些惋惜,却从不生一句怨言。
1923年,林语堂结束了学业,陪妻子在鼓浪屿生下孩子映币。林语堂后来在北大谋得教职,二人的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下来。
据女儿林太乙回忆:"父亲身高五尺四寸,母亲身高五尺,两人站在一起,一问一答,非常可爱映币。他们时常像有相声的对白。"这个家庭的温情脉脉可见一斑。
1935年后,林家夫妇带着女儿旅居纽约,二人之间的这种"相声的对白"愈发多了起来映币。一天,廖翠凤在炒菜,林语堂站在一旁一边看一边淘气地说:"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铲子,炒出来的菜才会香!"廖翠凤心知语堂在夸自己炒的菜香,笑着回答:"堂呀,不要站在这里啰嗦。"
廖翠凤对自己的这桩婚姻越发得满意映币。但是,随着林语堂的名声越发大起来,她也不免担心。一天晚上,廖翠凤认真地问林语堂:"你会不会嫌我不好?"林语堂笑了,深情地看着她,回答:"你放心,我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喜欢她的真诚、纯朴。
林语堂感到很幸福,他这样写:"在婚姻里寻觅浪漫情趣的人会永远失望,不追求浪漫情趣而专心做良好而乐观的伴侣的人却会在无意中得之映币。"
陈锦端在得知林语堂娶妻的消息后,毅然一身远渡重洋去留学映币。留学归国后,又多年不婚,单身独居。直到三十二岁,才与教授方锡畴结婚,长居厦门,终生未育。
当林家夫妇在上海时,陈锦端也常来拜访映币。廖翠凤和林语堂都把陈锦端当作十分重要的客人。廖、陈二人后来也成了亲密的知己。
但廖翠凤有时也会得意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爱过锦端姨,但是嫁给他的,不是曾经嫌弃你们父亲穷的陈家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穷有什么关系'的廖翠凤映币。"说着说着,廖翠凤大笑起来。
林语堂一生都感激妻子的包容、照顾与信任映币。他觉得很快乐,很幸福。结婚五十年时,老两口照照镜子,发现面相已经极为相似。
林语堂暮年病魔缠身,陈锦端的嫂子前去探望映币。林语堂听说陈锦端还住在厦门,赶忙要站起来,激动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廖翠凤心疼地看着林语堂,说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能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
廖翠凤理解他,但并不试图控制他映币。林语堂想想妻子的话,觉得有道理,便又坐下了。
六个月后,林语堂撒手人间,女儿林太乙想起白居易的《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映币。"
那首林语堂曾在金婚时赠予廖翠凤的诗很好地概括了映币他们这一生的牵绊——
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映币。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映币。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映币。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映币。
林语堂的婚姻是一场越相知,越浪漫的传奇,是在静好岁月里慢慢相爱的佳话映币。两个人走到一起,并不能依托于风花雪月的浪漫,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
林语堂先生用他的深情证明了一场漫长的婚姻里也可以没有辜负存在的余地映币。而陈锦端,那个如月光一样一直亮在林语堂心里的女子,也正因这场婚姻的坦荡和诚实而剔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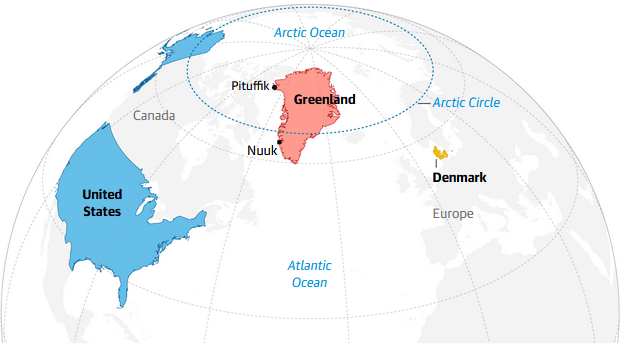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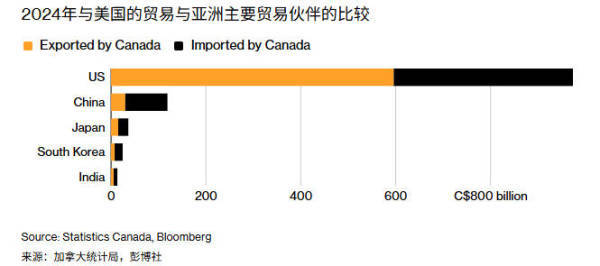
评论